在保護(hù)中原住民有多重要?
發(fā)布日期:2021-11-22
在說(shuō)起由原住民或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治理和管理的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時(shí),我們常會(huì)陷入疑惑:什么樣的人才能被稱為原住民?中國(guó)有原住民么?少數(shù)民族就是原住民么?如何辨別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的主體是原住民社區(qū)還是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?這兩者在國(guó)際法和保護(hù)實(shí)踐中又有什么差別?為何自我決定和自我認(rèn)同很重要?國(guó)際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聯(lián)盟的這篇文章也許可以提供某些答案,它還將有助于理解為何對(duì)于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的識(shí)別而言,社區(qū)對(duì)自身環(huán)境的關(guān)愛(ài)與長(zhǎng)久守護(hù)至關(guān)重要,而對(duì)于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的韌性和可持續(xù)性而言,公平公正地保障社區(qū)的各項(xiàng)基本權(quán)利是基礎(chǔ),無(wú)論這些社區(qū)自我認(rèn)定為是原住民的還是當(dāng)?shù)氐摹?/span>
什么是原住民
用一位原住民代表的話來(lái)說(shuō):“原住民(Indigenous peoples)幾乎生活在世界各大洲的所有國(guó)家,其包括了傳統(tǒng)的狩獵采集者、自給自足的農(nóng)民、法學(xué)家等各類人。原住民的人數(shù)在3億至5億之間,大概占據(jù)了世界陸地面積的20%,孕育和滋養(yǎng)了世界上80%的文化和生物多樣性”。[1]聯(lián)合國(guó)網(wǎng)站上對(duì)原住民的描述也同樣寬泛:“與人和環(huán)境相關(guān)的獨(dú)特文化和方式的繼承者與實(shí)踐者就是原住民,他們保留了不同于所居住地區(qū)主流社會(huì)的社會(huì)、文化、經(jīng)濟(jì)和政治特征”。因此,要準(zhǔn)確估算如今現(xiàn)存的原住民數(shù)量是相當(dāng)困難的。
1986年,聯(lián)合國(guó)人權(quán)委員會(huì)提議將原住民定為“在其領(lǐng)土上與被入侵和殖民前發(fā)展起來(lái)的社會(huì)具有歷史連續(xù)性的人”。國(guó)際勞工組織1989年通過(guò)第169號(hào)《獨(dú)立國(guó)家原住民和部落民公約》(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IndependentCountries)后,“時(shí)間因素”被進(jìn)一步強(qiáng)調(diào),原住民被譽(yù)為“擁有前輩所傳承下來(lái)的不成文的悠久習(xí)俗、信仰、儀式和實(shí)踐寶庫(kù)的傳統(tǒng)的人”。2007年《聯(lián)合國(guó)原住民權(quán)利宣言》(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, UNDRIP)[2]建議了一套也許有助于識(shí)別原住民的指導(dǎo)性特征,其中包括:自我認(rèn)同(self-identification)為原住民國(guó)家和/或人民;共同遭受過(guò)不公正、被殖民和土地被剝奪的歷史;復(fù)雜的基于地點(diǎn)的關(guān)系網(wǎng)絡(luò):語(yǔ)言、傳統(tǒng)習(xí)俗、知識(shí)以及有別于所居住國(guó)家主流形態(tài)的法律和文化制度(盡管如巴布亞新幾內(nèi)亞和玻利維亞等國(guó)家,原住民是其國(guó)家的主體人群);以及有助于可持續(xù)治理和管理人類與物質(zhì)及非物質(zhì)世界關(guān)系的知識(shí)、文化和實(shí)踐。此外,一些人還強(qiáng)調(diào)把以下特征也作為原住民特性(indigeneity):“保留了類似原住民特征的祖先的習(xí)俗和傳統(tǒng)”,“即使只是形式上,被置于國(guó)家的結(jié)構(gòu)之下,這個(gè)結(jié)構(gòu)里包含了與自己不同的國(guó)家、社會(huì)和文化特征”。
UNDRIP基于人民 (people)來(lái)說(shuō)原住民(Indigenous peoples),是因?yàn)槿嗣癖徽J(rèn)為是國(guó)際法的主體,其集體自決權(quán)是被1966年的《聯(lián)合國(guó)公民權(quán)利和政治權(quán)利國(guó)際公約》以及《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(huì)和文化權(quán)利國(guó)際公約》維護(hù)的。盡管國(guó)際上認(rèn)可原住民的集體權(quán)利,但在國(guó)家層面,今天并不是所有原住民都被承認(rèn)為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集體權(quán)利的擁有者。

圖1:婆羅洲島高地上的原住民社區(qū)在為生態(tài)旅游的訪客準(zhǔn)備其特色美食。這些高地原住民為了保護(hù)婆羅洲之心的山地?zé)釒в炅忠黄鹜苿?dòng)成立了原住民聯(lián)盟FORMADAT,并因此獲得了2015年的UNDP赤道獎(jiǎng)。對(duì)于這些indigenous people,中國(guó)過(guò)去一般翻譯為“土著”,作為一個(gè)術(shù)語(yǔ),其政治文化內(nèi)涵和運(yùn)用在不同的國(guó)家地區(qū)、不同的語(yǔ)境和場(chǎng)景中可能都不同。
過(guò)度包容或包容度不夠的例子
以上原住民的眾多定義包含了一系列納入或排除的標(biāo)準(zhǔn),以至于可能會(huì)產(chǎn)生過(guò)度包容或包容度不夠的情況。如果原住民的定義只基于與被殖民前社會(huì)的聯(lián)系,那么除了殖民者的直接后裔,那些生活在曾被殖民者征服的國(guó)家里的人就都可以被視為原住民。例如,所有菲律賓人都可以因此被認(rèn)為是原住民,因?yàn)樗麄兪?quot;曾居住在現(xiàn)有領(lǐng)土上的人民的現(xiàn)存后裔"。然而,殖民統(tǒng)治導(dǎo)致許多菲律賓人已丟棄了他們的文化傳統(tǒng),和自然失去了緊密的聯(lián)系,也不再有效保護(hù)其領(lǐng)土上的自然生靈。與之相反,生活在菲律賓科迪勒拉和呂宋島上的許多伊哥洛特人(Igorots)與大部分菲律賓人不同,他們“完整保留了其祖先的習(xí)俗和傳統(tǒng)”。事實(shí)上,根據(jù)Reyes(2017)的說(shuō)法:“根據(jù)國(guó)際法,這些人是普遍有權(quán)享有原住民特定權(quán)利的群體”。
在區(qū)分原住民還是非原住民時(shí),背景因素顯得尤為重要。前原住民權(quán)利問(wèn)題特別調(diào)查員James Anaya指出:“如果只是從一般意義上去理解原住民,而不考慮特定的背景因素,就很難區(qū)分哪些尼泊爾人是原住民,哪些不是。例如,尼泊爾沒(méi)有被外國(guó)勢(shì)力殖民的歷史,因此,即使不考慮他們與土地的密切聯(lián)系和強(qiáng)烈的歸屬感,他們要么全部都可以被認(rèn)為是原住民要么全都不是。”不過(guò),他認(rèn)為尼泊爾的阿迪瓦西·賈納賈提人(Adivasi Janajati)是原住民,因?yàn)樗麄兣c其他大多數(shù)的尼泊爾人不同,他們自我認(rèn)同為不同的族群,歷史上他們也被排除在占主導(dǎo)地位的社會(huì)和宗教等級(jí)制度之外,有自己獨(dú)特的語(yǔ)言和傳統(tǒng)習(xí)俗。
國(guó)際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聯(lián)盟則強(qiáng)調(diào)自我認(rèn)同(self-identfication)是原住民特性的必要條件,并最終建議以原住民自己認(rèn)定的名稱來(lái)指稱他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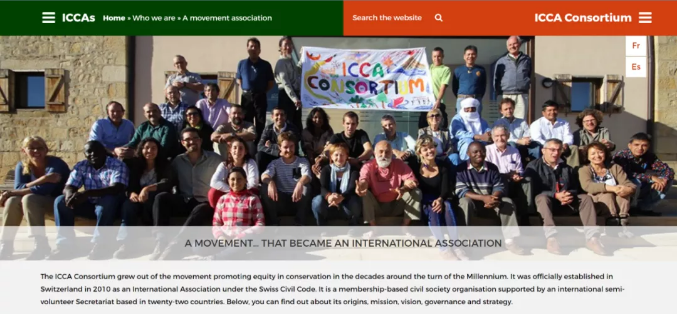
圖2:國(guó)際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聯(lián)盟(The ICCA consortium)的網(wǎng)站介紹(www.iccaconsortium.org)。聯(lián)盟2010年在瑞士注冊(cè),源起于2000年左右推動(dòng)保護(hù)中的平等的全球運(yùn)動(dòng),是一個(gè)由全球一百多個(gè)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和相關(guān)NGO作為會(huì)員的社會(huì)公益組織。
什么是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?
在提到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(英文簡(jiǎn)稱ICCAs)時(shí),人們的首要問(wèn)題之一往往是:這是誰(shuí)的?誰(shuí)把它作為一個(gè)特別的地方挑選了出來(lái)并建立了它?誰(shuí)為它命名?誰(shuí)一直以來(lái)治理、管理和守護(hù)著它?有時(shí)答案涉及原住民悠久歷史和神圣源起的敘述...但如果答案是“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”(local communities),一下就會(huì)變得模糊起來(lái)。
然而,“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”不僅在人類學(xué)、社會(huì)和經(jīng)濟(jì)意義上至關(guān)重要,而且在法律意義上也愈發(fā)重要。事實(shí)上,文獻(xiàn)對(duì)“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”的定義多種多樣。國(guó)際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聯(lián)盟的成員通常用的都是些實(shí)用的定義,也理解它和原住民之間的差異:簡(jiǎn)單來(lái)說(shuō),我們認(rèn)為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是那些通常并不把自己看成原住民的社區(qū)(盡管在一些國(guó)家,有些是為了在策略上避免與原住民相關(guān)的邊緣化和污名化才這么做的)。不過(guò),也有一些評(píng)論員認(rèn)為,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與原住民之間是有客觀差異的,即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嚴(yán)格用原住民特性來(lái)檢驗(yàn)并不完全符合(值得注意的是,自我定義和特定的檢驗(yàn)要求,這兩者是非常不同的)。在某些國(guó)家,甚至包括UNDRIP的簽署國(guó),原住民甚至被概化為“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”來(lái)避免遵守如《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》中的相關(guān)程序要求。
2011年,生物多樣性公約(簡(jiǎn)稱CBD)的第14次締約國(guó)大會(huì)召開(kāi)了一次特別專家會(huì)議來(lái)闡明“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”這個(gè)術(shù)語(yǔ)的使用。CBD在報(bào)告中聲明,這個(gè)術(shù)語(yǔ)的含義模棱兩可,不同國(guó)家的法律解釋也各不相同(例如,有的解釋為一群有著集體法人資格的人,有的則為由公益組織或公民社會(huì)組織法定代表的一群人)。報(bào)告著重強(qiáng)調(diào)自我認(rèn)同是確定誰(shuí)是原住民誰(shuí)是當(dāng)?shù)鼗?且傳統(tǒng)社區(qū)的最合適的方法,而且強(qiáng)調(diào),在國(guó)際法中,定義并不是保護(hù)的先決條件。因此,CBD在使用“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”這個(gè)詞時(shí),指的是與其傳統(tǒng)居住或使用的土地與水都有著長(zhǎng)期聯(lián)系的社區(qū),無(wú)論是否存在一個(gè)普遍被接受的定義,其集體權(quán)利都應(yīng)該得到認(rèn)可。

圖3:位于云南麗江的黎光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是國(guó)內(nèi)第一個(gè)通過(guò)了同行評(píng)審在UNEP-WCMC全球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注冊(cè)系統(tǒng)內(nèi)注冊(cè)的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(ICCAs)。在頒證儀式上,傈僳族村民們從聯(lián)合國(guó)官員手中接過(guò)了證書。“原住民”是20世紀(jì)后期在全球化浪潮下,學(xué)術(shù)界和國(guó)際社會(huì)在對(duì)殖民、工業(yè)化和全球化的反思下,出于對(duì)文化多樣性保護(hù)及弱勢(shì)群體權(quán)益保障的關(guān)切而提出的概念,但并無(wú)統(tǒng)一和普遍接受的定義。我國(guó)有關(guān)民族或少數(shù)民族問(wèn)題的正式用語(yǔ)中也沒(méi)有“原住民”這個(gè)用法。
國(guó)際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聯(lián)盟對(duì)“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”的定義是:“一個(gè)自我認(rèn)同的人類群體,其集體行動(dòng)以有助于在漫長(zhǎng)的時(shí)間內(nèi)確定領(lǐng)土和文化的方式進(jìn)行”。一個(gè)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既可以是長(zhǎng)期存在的(“傳統(tǒng)的”)也可以是相對(duì)較新的,既可以是單一民族也可以包含多個(gè)民族,通常通過(guò)自然繁衍、關(guān)心親緣關(guān)系和愛(ài)護(hù)生活環(huán)境來(lái)保證其延續(xù)性。這個(gè)概念里的社區(qū)既可能是永久定居的,也可能是遷徙流動(dòng)的。盡管遷徙的社區(qū)對(duì)特定地點(diǎn)的依戀與定居社區(qū)一樣強(qiáng)烈,但它們通常不被人們稱為“當(dāng)?shù)氐摹保驗(yàn)檫@些地點(diǎn)可能會(huì)隨季節(jié)發(fā)生巨大變化。
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的成員通常有頻繁地直接接觸的機(jī)會(huì)(可能是面對(duì)面),并擁有共同的社會(huì)和文化元素,如共同的歷史、傳統(tǒng)、語(yǔ)言、價(jià)值觀、生活計(jì)劃和/或認(rèn)同感。這些元素將他們綁定在一起并有別于社會(huì)中的其他部分。通常大家都很清楚社區(qū)由誰(shuí)組成,誰(shuí)參與和/或響應(yīng)其治理系統(tǒng),誰(shuí)是誰(shuí)不是。社區(qū)的大多數(shù)成員擁有與特定領(lǐng)土或地區(qū)的清晰而強(qiáng)大的歷史、文化、精神等聯(lián)系。這些聯(lián)系可能來(lái)自于定居、自然資源的使用(永久的、季節(jié)性的、季節(jié)性遷徙放牧或游牧的),或僅僅是文化和精神上的依戀和責(zé)任感。
一個(gè)社區(qū)的經(jīng)濟(jì)組織通常反映了其在當(dāng)?shù)丨h(huán)境和資源上的共同利益,也往往包含了公共池塘資源管理(common pool resources management)的要素和因地制宜的資源分配規(guī)則。對(duì)于社區(qū)成員是否能集體行動(dòng)來(lái)增進(jìn)共同利益而言,凝聚力、共同的認(rèn)同感以及利益共享至關(guān)重要。
一個(gè)運(yùn)轉(zhuǎn)的社區(qū)通常擁有地方“行政”制度以及一個(gè)其成員認(rèn)為正當(dāng)合法的“政治”領(lǐng)導(dǎo)層。通過(guò)這些,社區(qū)能對(duì)是否遵守商定的規(guī)則以及沖突的解決進(jìn)行控制。許多社區(qū)成員也承認(rèn)自己擁有一個(gè)共同的政治身份,這使得他們能對(duì)他們的領(lǐng)土和鄰居行使和/或要求集體權(quán)利與責(zé)任。領(lǐng)導(dǎo)力、合法性和凝聚力通常也要求在空間上或通過(guò)資源獲取的準(zhǔn)入/準(zhǔn)出規(guī)則來(lái)劃定社區(qū)的管轄邊界。
社區(qū)的制度、規(guī)則甚至領(lǐng)土,通常都是動(dòng)態(tài)的、因地制宜的和不斷變化的,這個(gè)事實(shí)使得社區(qū)能隨時(shí)間的流轉(zhuǎn)而強(qiáng)化其適應(yīng)能力和韌性(resilience)。

圖4:廣西渠楠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觀。渠楠通過(guò)有效的治理和管理,保護(hù)著30多群全球極度瀕危的白頭葉猴及其棲息地。這里的喀斯特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,不僅是白頭葉猴等野生動(dòng)植物的庇護(hù)所,也是這些壯族老百姓的精神和物質(zhì)家園 。?宋晴川
區(qū)分有那么重要嗎?
盡管原住民和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有許多共同的特點(diǎn),但他們自我認(rèn)同為哪一種,法律上的結(jié)果卻有不同。原住民被承認(rèn)為國(guó)際法的主體,而且在國(guó)際法和通常的國(guó)家法律中,他們被認(rèn)為是集體權(quán)利的擁有者。這種集體權(quán)利集中在其自決權(quán)上,并立基于其原住民特性。這些權(quán)利通常不賦予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,并不以"過(guò)著可持續(xù)的生活"(living sustainable lives)為條件。
有趣的是,美洲人權(quán)法院最近在處理兩起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的案件時(shí),認(rèn)為其與原住民享有同樣的權(quán)利。具體來(lái)說(shuō),2005年莫伊瓦納(Moiwana)村訴蘇里南(Suriname)案,以及2007年薩拉馬卡人(Saramaka people)訴蘇里南(Surinmae)案中,法院承認(rèn)兩個(gè)由前非洲奴隸的后裔組成的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是其祖?zhèn)魍恋氐暮戏〒碛姓撸M管他們不擁有法律文書。在這之前,2001年馬亞尼亞(蘇摩)阿瓦斯廷尼(Mayagna (Sumo) Awas Tingni)村訴尼加拉瓜案,依據(jù)的也是同樣的法理。只不過(guò)案件是關(guān)于原住民的。
盡管有這些法庭的判例,但國(guó)際法似乎仍然在承認(rèn)集體權(quán)利上將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和原住民區(qū)分開(kāi)。而另一方面,《里約宣言》第22項(xiàng)原則指出:“原住民和他們的社區(qū)與其他的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,都因?yàn)樗麄兊闹R(shí)和傳統(tǒng)實(shí)踐而在環(huán)境管理和發(fā)展中起著關(guān)鍵作用。國(guó)家應(yīng)該認(rèn)可并恰當(dāng)?shù)刂С炙麄兊纳矸菡J(rèn)同、文化和利益,并使他們有能力去有效參與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”。
與此相呼應(yīng),“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”這一概念得到了CBD第8j號(hào)條款的承認(rèn),并在此后的聯(lián)合國(guó)機(jī)構(gòu)、聯(lián)合國(guó)條約和其他國(guó)際組織發(fā)布的諸多其他國(guó)際文件中出現(xiàn),如名古屋議定書、國(guó)際熱帶木材協(xié)定、農(nóng)業(yè)植物遺傳資源國(guó)際條約、聯(lián)合國(guó)海洋法公約、防治荒漠化公約、拉姆薩濕地公約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所有這些國(guó)際文件中,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是因?yàn)樗鼈兣c環(huán)境的關(guān)系,而不僅僅因?yàn)樗鼈冏鳛樯鐓^(qū)的存在而出現(xiàn)。
國(guó)際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聯(lián)盟尊重人們的自我定義,無(wú)論是原住民還是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。不管怎么定義,對(duì)于這些守護(hù)著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及其自然生命的人們,聯(lián)盟都在為確保其長(zhǎng)期的居住權(quán)而努力。

圖5: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(ICCAs)的三個(gè)識(shí)別標(biāo)準(zhǔn)。ICCAs是territories and areas governed,managed and conserved by custodia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(中文直譯為作為守護(hù)者的原住民或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所治理、管理和有效保護(hù)的領(lǐng)土或地區(qū))的簡(jiǎn)稱,中文翻譯為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。20年前ICCAs的名稱是CCAs,是Community Conserved Areas的縮寫。后來(lái)補(bǔ)充了字母“I”來(lái)強(qiáng)調(diào)作為守護(hù)者的原住民的作用,而且還強(qiáng)調(diào)了他們擁有的是領(lǐng)土而不只是土地。最近國(guó)際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聯(lián)盟內(nèi)的成員開(kāi)始用生命之域(territories of life)來(lái)稱呼ICCAs, 這是為了表達(dá)他們所關(guān)愛(ài)的環(huán)境有著多姿多彩的生命和多維特征。不過(guò),ICCAs已作為一種對(duì)此現(xiàn)象的可視化的術(shù)語(yǔ)表達(dá)而保留下來(lái)并使用在國(guó)際政策中。
兩者好區(qū)分么?
區(qū)分原住民和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很重要,但有時(shí)卻非常困難。一個(gè)錯(cuò)綜復(fù)雜的案例是,在剛果民主共和國(guó),法律只承認(rèn)俾格米人是原住民,而其他群體都被看作是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,理由是俾格米人被認(rèn)為是最早的定居者。然而,一些非俾格米人聲稱,早在俾格米人來(lái)之前,他們就已占領(lǐng)了一些森林。另一方面,國(guó)家的法律也沒(méi)能預(yù)見(jiàn)到對(duì)原住民和當(dāng)?shù)厣鐓^(qū)的區(qū)別對(duì)待,也忽視了國(guó)際法對(duì)承認(rèn)原住民特殊權(quán)利的要求。此外,在同一地點(diǎn),俾格米人與其他種族之間有著很強(qiáng)的文化紐帶,存在許多混居的、不同族群角色不同的社區(qū),其中對(duì)待俾格米人從不尊重到精神奴役的各種情況都有。也有非俾格米人聲稱自己是俾格米人的情況,以便分享一些俾格米人的傳統(tǒng)精神力量和角色,尤其是和領(lǐng)土和自然資源有關(guān)的。
編譯:張穎溢
原文(除圖片及圖片注釋外)見(jiàn):Sajeva G., G. Borrini-Feyerabend and ThomasNiederberger, 2019. Meanings and more... Policy Brief of the ICCA Consortium no. 7. The ICCA Consortium in collaboration with CENESTA P10-14.
注釋:
1. Reyes,2017引用的原住民的數(shù)量是由其它幾位作者估算的。然而要想追溯比Sobrevila(2008,第5和50頁(yè))更可靠的數(shù)據(jù)源頭卻非常困難,因?yàn)槠湟玫奈恼耊RI(2005)再往前已不可考。國(guó)際社區(qū)保護(hù)地聯(lián)盟因此沒(méi)有理由相信這里引用的數(shù)據(jù)是錯(cuò)誤的,但也建議參考Alden Wily(2011)和Garnett et al.(2018)的工作來(lái)佐證。關(guān)于文化多樣性,Sobrevila(2008,第3和52頁(yè))實(shí)際上說(shuō)95%的文化多樣性是由只占世界人口4%的5000多個(gè)民族呈現(xiàn)出來(lái)的,但這個(gè)數(shù)據(jù)很少被引用。
2. 宣言指出各國(guó)政府可根據(jù)附件和第46條自行確定原住民的定義。宣言雖無(wú)國(guó)際法的約束力,但聯(lián)合國(guó)認(rèn)為宣言設(shè)定了對(duì)待原住民的重要標(biāo)準(zhǔn),對(duì)消除對(duì)原住民的人權(quán)侵犯并幫助其克服歧視和邊緣化是一個(gè)重要工具。出于各國(guó)社會(huì)、政治和經(jīng)濟(jì)的現(xiàn)實(shí)情況差異及劃分群體本身是否有助于提升該群體的福祉和發(fā)展的考慮,學(xué)者們對(duì)是否要給原住民以明確的定義和劃分也有爭(zhēng)議。(編者注)


















